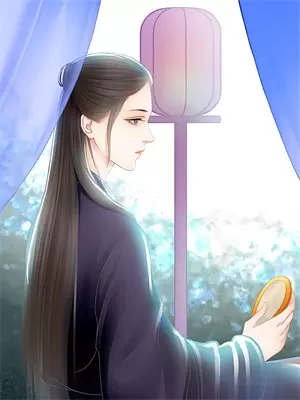1 屠宰场惊魂他说那是精神病院,可医生白袍在渗血被囚禁在屠宰场三个月后,
我终于撬开通风管道逃生。 警察接到报案赶来,却严肃地告诉我:“先生,
那里是废弃精神病院。” 他们带我回现场确认,
病院档案室竟有我的病历—— “患者坚信自己被困屠宰场,幻想听到电锯声和猪的惨叫。
” 主治医生温柔地递给我药片:“该吃药了,别怕,这里很安全。” 直到今早醒来,
我发现病房墙壁渗出猪血般的污渍。 而医生白大褂的衣角,别着一把沾满肉屑的屠宰钩。
冰冷的铁锈味混杂着某种难以言喻的腥臊,成了这三个月来我唯一熟悉的空气。
我蜷缩在角落,黑暗中,粘腻的地面浸透了单薄的裤料,寒意刺骨。远处,不,
也许就在隔壁,那持续不断的、富有节奏的“嗡——嘶——”声再次响起,
那是电锯咆哮后的余韵,伴随着偶尔传来的、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嚎,还有……猪的惨叫。
对,猪的惨叫,被拖向死亡时那种绝望的、撕裂一切的哀鸣。它们混杂在一起,日复一日,
夜复一夜,几乎要把我的脑髓都搅成浆糊。三个月。或许更久?时间在这里早已失去刻度。
我只记得被掳来那天,后脑勺遭到重击,醒来就在这片人间地狱。这里是个屠宰场,
毫无疑问。我见过那些穿着厚重胶皮围裙、戴着金属面罩的身影,
他们拖着软绵绵的人形物体,或是挣扎嘶吼的活物,
走向走廊尽头那扇永远淌着暗红色液体的铁门。铁门后面,
是更浓重的血腥和更刺耳的机械运作声。我不能死在这里。不能像那些猪一样。
求生的本能像微弱的火苗,在绝望的寒夜里摇曳,却从未熄灭。我观察,用尽一切感官。
送来的馊饭是从一个固定的、带有栅栏的洞口推进来;脚步声总在固定的时间响起,两次,
间隔很长;唯一的通风口,在靠近天花板的高处,很小,覆盖着满是油污的铁丝网,
但……有风,极其微弱,带着一丝外面世界的气息。就是它了。
太钝的金属片——大概是某个倒霉鬼遗落在地上的勺柄——开始对付通风口边缘的锈蚀螺钉。
黑暗中,每一次金属刮擦的细微声响都让我胆战心惊,生怕引来那些“屠夫”。手腕酸麻,
虎口被磨破,血和锈混在一起,结成硬痂。一天,两天?不知道。
时间只剩下“之前”和“之后”的区别。终于,最后一颗螺丝松动了。就是现在!
我用尽全身力气,猛地向上顶开铁丝网,冰冷而相对新鲜的空气涌入鼻腔,几乎让我晕厥。
顾不上许多,我手脚并用地扒住边缘,瘦削的身体爆发出最后的力量,艰难地钻了进去。
管道狭窄,布满灰尘和蛛网,只能匍匐前进。身后,似乎传来了脚步声和呵斥,但我不管了,
只是拼命地向前爬,向前爬,任由锋利的金属边缘划破皮肤,留下火辣辣的疼痛。
不知过了多久,前方出现了一丝微弱的光亮。我用头撞开另一端的覆盖物,重重地摔落在地。
刺眼的光芒让我瞬间失明,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我却贪婪地呼吸着,
肺部像破风箱一样剧烈起伏。自由!是自由的味道!我连滚带爬地冲到马路边,挥舞着双臂,
状若疯癫。一辆车疾驰而过,溅了我一身泥水。第二辆,第三辆……终于,一辆车停了下来。
好心的司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我,帮我报了警。警灯闪烁,红蓝的光晕切割着雨夜。
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下了车,他们的脸在灯光下显得严肃而刻板。“先生,你没事吧?
”一个年长些的警察开口,声音平稳,带着公事公办的疏离。我抓住他的胳膊,语无伦次,
声音嘶哑得可怕:“屠宰场……就在那边!他们……他们杀人!杀猪!
电锯……一直响……三个月了……”年轻点的警察皱了皱眉,用手电筒照了照我来的方向,
又和同伴交换了一个眼神。“先生,你先冷静点。”年长警察试图安抚我,
“你说的是哪个方向?”我急切地指向那片吞噬了我三个月的黑暗区域:“那边!
那个废弃的工厂……不,屠宰场!”两个警察的表情更加古怪。年长警察沉默了一下,
似乎在斟酌词句,然后非常严肃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先生,我想你弄错了。
那个方向,只有一家废弃了很久的建筑——是市精神病院。”精神病院?
2 真相还是幻觉这三个字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扎进我的颅骨。我愣住了,
浑身的血液似乎瞬间凝固。“不……不可能!”我尖叫起来,抓住他胳膊的手更加用力,
“我亲眼看见的!我听到了!闻到了!那是屠宰场!”“先生,你情绪不太稳定。
”年长警察试图挣脱我的手,语气依旧克制,“这样吧,我们带你过去确认一下,
也许能帮你……理清思路。”理清思路?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认为我疯了!
一股混杂着愤怒、恐惧和巨大荒谬感的寒意从脚底窜上头顶。但我没有选择。
我必须证明给他们看。警车行驶在泥泞的路上,最终停在一栋巨大、轮廓阴森的建筑物前。
哥特式的尖顶在雨夜中像魔鬼的犄角,斑驳的墙体,大部分窗户都黑洞洞的,
破碎的玻璃像残缺的牙齿。铁门歪斜地挂着生锈的锁链,周围杂草丛生。
这……这明明就是我逃出来的地方!可外观,不知为何,
确实透着一股老式精神病院特有的、令人不安的死寂,而非屠宰场那种赤裸裸的工业暴力感。
警察用手电筒照亮门廊上几乎被藤蔓覆盖的铭牌。剥开苔藓,
模糊的刻字显现出来——“清河精神病院”。“看,我没说错吧。
”年长警察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这里废弃快十年了。”他们撬开锈蚀的铁锁,
推开吱呀作响的大门。一股陈腐的灰尘味扑面而来,
混合着消毒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类似福尔马林的气息。手电光柱在空旷的大厅里晃动,
照亮剥落的墙皮、翻倒的废弃轮椅、散落一地的泛黄纸张。没有血,没有肉钩,没有电锯,
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和破败。“不……不是这样的……”我喃喃自语,心脏狂跳。这里的布局,
明明就是我爬过的通风管道所在的建筑!“先生,你需要帮助。
”年轻警察的语气带着一丝怜悯,这怜悯比直接的质疑更让我心寒。
“档案室……”我猛地抓住一丝希望,“一定有记录!看看有没有我!或者……或者别的!
”年长警察沉吟片刻,似乎觉得这是个让我死心的好办法。他们根据指示牌,
找到了位于二楼的档案室。门没锁,里面文件柜东倒西歪,纸张散落得到处都是。
警察们似乎也起了点好奇心,开始用手电筒随意翻找。突然,年轻警察“咦”了一声,
从一堆散落的文件夹里抽出一份。他用手电光聚焦在封面上。那上面,清晰地写着一个名字。
是我的名字。照片,是我一年前失踪时拍的工作照,面带微笑,精神焕发。警察的眼神变了,
从之前的怀疑、怜悯,变成了某种确认后的凝重,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
他们把档案递到我面前。我颤抖着接过,借着冰冷的光线,看向那些打印的字迹。
姓名:[我的名字] 诊断:急性妄想障碍,伴幻觉及现实解体症状。
主要症状:坚信自己被囚禁于非法屠宰场,
持续产生被追杀、听到电锯声、猪的惨叫声等幻听幻视,并伴有强烈的被害妄想。
否认自身精神状况,坚信所见所闻为真实。
入院日期:[正好是三个月前] 主治医师:林医生。下面还有详细的病程记录,
描述“患者”如何绘声绘色地描述屠宰场的细节,如何试图逃跑,
如何攻击“医护人员”……“不!这不是真的!”我像被烫到一样扔掉档案,纸张散落一地,
“是伪造的!是他们伪造的!为了掩盖这里的真相!”脚步声从走廊传来,沉稳,清晰。
一个穿着洁白医生袍的男人走了进来,大约四十岁年纪,戴着金丝眼镜,面容温和,
眼神里带着一种专业的、令人安定的关切。“警察先生,谢谢你们。”他对着警察微微点头,
然后看向我,声音温柔得如同春水,“[我的名字],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是林医生。病历上的那个名字。他蹲下身,与我平视,伸出手,
掌心躺着几颗白色的药片:“你看,你又不按时吃药了。所以才会产生这些可怕的幻觉,
跑到这种危险的地方来。别怕,没事了,跟我回去,这里很安全。”他的眼神那么真诚,
语气那么恳切,连旁边的警察似乎都松了口气,仿佛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责任人。
“不……你撒谎!”我惊恐地向后退,脊背撞上冰冷的文件柜,“你们是一伙的!
你们都是屠夫!”林医生脸上掠过一丝恰到好处的难过和无奈,
他转向警察:“他的病情又加重了。需要立刻进行镇静和治疗。麻烦二位帮忙,
把他送回病房吧。”两个警察对视一眼,点了点头。他们一左一右地架住了我。我拼命挣扎,
嘶吼,咒骂,用尽全身力气,但数月的囚禁和营养不良让我虚弱不堪。
我的反抗在他们手中如同困兽之斗。“那里是屠宰场!是地狱!放开我!
”我的哭喊在空旷破败的档案室里回荡,
却只换来警察更用力的钳制和林医生温和却不容置疑的安抚:“好了,好了,安静下来,
吃药就好了……”我被强行拖离了档案室,拖过幽暗的走廊,拖向我刚刚拼死逃离的深渊。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我最后的意识。3 白袍下的屠夫……再次恢复意识时,
我躺在一张冰冷的铁床上。头顶是惨白的天花板,刺眼的日光灯管嗡嗡作响。房间很小,
墙壁是那种老旧的、刷着浅绿色油漆的样式,已经大面积剥落,露出底下灰黑的底色。
唯一的门是厚重的金属门,中间有一个带着栅栏的小窗口。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味道,
试图掩盖什么,却反而让那丝若有若无的、熟悉的血腥气变得更加可疑。是病房。标准的,
精神病院的病房。难道……难道真的是我疯了?那些电锯声,猪的惨叫,淋漓的鲜血,
冰冷的肉钩……全都是我病态大脑虚构出来的产物?那份病历,那些记录,警察的确认,
林医生无可挑剔的关切……这一切,难道才是真相?
巨大的认知混乱和自我怀疑几乎将我撕裂。我蜷缩起来,把头埋进膝盖,
发出受伤野兽般的呜咽。不知过了多久,门上的小窗口被拉开,一双眼睛冷漠地扫了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