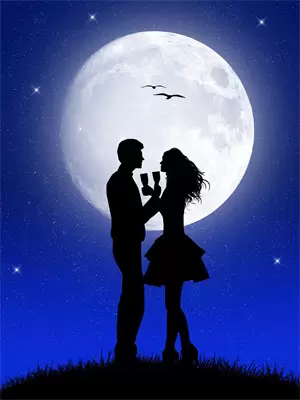重生回到二十岁,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考研资料。上辈子卷成首席分析师,
结果过劳猝死在办公桌前。这辈子我决定换个赛道,
直接瞄准楼下咖啡店那位身价百亿的年轻寡妇。当同事还在为升职加薪挤破头时,
我已住进她的山顶别墅。每天种花钓鱼,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直到那天,
她前夫的家族找上门来……江屿猛地睁开眼。映入眼帘的不是医院惨白的天花板,
也不是地狱油锅的幻象,而是……宿舍?头顶是有些发黄的天花板,老式吊扇慢悠悠地转着,
发出规律的嘎吱声。空气里弥漫着隔夜泡面混合着男生宿舍特有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
书桌上,笔记本电脑还亮着屏幕,旁边是堆成小山的金融学教材和考研英语红宝书。
他僵硬地转动脖子,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日程表:早上六点半起床背单词,
七点半到图书馆占座,
积分、宏观经济学、投资学……晚上十一点熄灯后还要打着手电筒再看一小时公司财报分析。
日期栏里,清晰地印着:20XX年3月15日。二十岁。大三下学期。考研冲刺的起点。
江屿抬起自己的手,年轻,骨节分明,带着长期握笔留下的薄茧,充满了力量。可他的记忆,
却停留在三十八岁那间宽敞奢华、却冰冷彻骨的独立办公室里。眼前最后闪过的,
是电脑屏幕上未完成的季度报告,心脏骤然紧缩的剧痛,以及身体砸在地毯上那沉闷的一声。
过劳死。卷了十八年,从寒门学子卷成名校高材生,再卷进顶级投行,
最后卷到首席分析师的位置。年薪千万,光环加身,是无数人眼中的成功典范。
可那又怎么样?他连花钱的时间都没有,赚来的财富只是个冰冷的数字,最终换来的,
是三十八岁就戛然而止的人生。一种巨大的荒谬和疲惫感,如同深海巨浪,瞬间将他吞没。
他喘着粗气,从那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坐起来。胸腔里那颗年轻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
提醒着他这不是梦,是真实的、失而复得的生命。他走到书桌前,
手指拂过那些崭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考研资料。曾几何时,
这些书本承载着他和他家庭的全部希望,是跨越阶层的唯一阶梯。
他为之付出了全部青春、健康,乃至生命。可现在,他看着它们,只觉得可笑。重活一世,
还要沿着这条注定通往地狱的老路再走一遍?不。绝不。江屿的眼神从最初的迷茫、震惊,
逐渐变得冰冷而坚定。他拿起那本厚厚的《公司金融》,掂了掂分量,
然后毫不犹豫地走到窗边,推开窗户。清晨微凉的空气涌进来,
带着楼下桂花树若有若无的香气。他手臂一扬,那本凝聚了无数人梦想的“敲门砖”,
划出一道抛物线,精准地落进了楼下的垃圾桶里。“啪嗒”一声轻响,
如同一个仪式开始的信号。
接着是《投资学》、《货币银行学》、《考研英语词汇》……一本接一本,
被他毫不留恋地扔了出去。堆满了书桌的“精神食粮”,转眼间变成了垃圾桶里的废纸。
同寝室的哥们儿被动静吵醒,迷迷糊糊地探出头:“我靠,江屿你疯了?不考研了?
”江屿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过身,
脸上是一种他们从未见过的、近乎解脱的轻松笑容:“不考了。换个活法。”“换什么活法?
去找工作?现在就业形势多差啊!”“找个班上?”江屿嗤笑一声,走到衣柜前,
开始翻找看起来最体面的一件衬衫,“那也太累了。”“那你想干嘛?”江屿换上衬衫,
对着宿舍里那块模糊的镜子整理衣领,镜中的年轻人眉眼锐利,
却带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静和沧桑。“我啊,”他慢条斯理地说,语气平淡,却掷地有声,
“去找个富婆,提前退休。”宿舍里陷入一片死寂,随后爆发出哄堂大笑。
“哈哈哈江屿你他妈真行!还没睡醒吧?”“就咱们这条件,哪个富婆看得上?
”“你小子受什么刺激了?”江屿没有理会室友们的调侃和质疑。他们不懂。
经历过地狱的人,才知道阳光有多么珍贵。用尊严换安逸?
上辈子他倒是保有了所谓的“尊严”,结果呢?尊严能当药吃,让他从猝死的边缘活过来吗?
他需要的不是另一个高压的战场,而是一个安全的港湾,一个能让他这艘差点沉没的破船,
彻底休养生息的地方。而目标,他早已锁定。就在学校后门那条商业街的转角,
有一家名叫“拾光”的咖啡店。店主是个年轻女人,叫沈静澜。看上去温婉安静,
不太与人深交。学校里关于她的传闻很多,最靠谱的一个版本是:她是个寡妇,丈夫早逝,
留给她一笔惊人的遗产,具体数额无人知晓,但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她选择在这大学城边开个不温不火的咖啡店,更像是某种避世和寄托。上辈子,
江屿偶尔去那里买杯美式,熬夜刷题时,曾不经意间瞥见过她放在柜台里的护照,
某个以富豪避税和隐私著称的岛国国籍。也曾在财经新闻的角落,
看到过她亡夫家族企业的模糊报道,那是真正的庞然大物。二十岁的穷学生,
只会把这些当作遥不可及的谈资。但三十八岁、在资本圈沉浮多年的江屿,
却能从那些碎片信息中,拼凑出真相的轮廓——一个身价至少百亿,
且目前情感和生活处于空窗期的年轻富婆。对现在的他而言,沈静澜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
而是一个清晰、明确、且极具可行性的……人生解决方案。接下来的日子,
江屿彻底变了个人。他退了考研班,辞掉了所有的兼职,甚至连专业课都开始选择性逃课。
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攻略富婆”这项伟大事业中。这当然不是无脑的跪舔。
上辈子能混到那个位置,江屿最擅长的就是分析、规划和精准执行。
他把沈静澜当作一个最重要的“客户”或者“投资项目”来研究。
他摸清了她咖啡店的营业规律上午十点开门,下午四点基本就不怎么管了,
她的喜好偏爱手冲咖啡,尤其是一种叫“瑰夏”的豆子;喜欢安静,
看书时讨厌被打扰;对甜度敏感,咖啡通常只加一点点糖,
她的生活习惯每周三下午会去一家高端花艺工作室,周五晚上会独自去看一场艺术电影。
他计算好了自己出现的频率和时机,既不能太频繁引起反感,又要恰到好处地刷足存在感。
于是,沈静澜渐渐熟悉了这样一个顾客:一个看起来很干净、很安静的男大学生,
总是出现在工作日的上午,店里没什么人的时候。他总是点一杯最便宜的美式,
然后坐在靠窗的角落,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喧哗,或者拼命敲电脑,
更多的时候,他只是看着窗外发呆,
或者拿一本看起来很深奥的原版书慢慢地读江屿从图书馆精心挑选的,
符合她可能品味的哲学或艺术类书籍。偶尔,店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时,
他会尝试进行一些简短、得体、绝不冒犯的交流。比如,称赞今天的手冲咖啡风味很好,
或者在她搬动一盆有点重的绿植时,自然地起身帮忙。他展示的不是殷勤,
而是一种恰到好处的分寸感、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以及一种……不易察觉的脆弱感。
他会在连续出现几天后,“偶然”地让她听到他打电话,
语气疲惫地婉拒某个听起来很诱人但需要拼命的内推机会,
或者“不小心”让她看到手机屏幕上,家庭群里关于经济困难的只言片语。
他要塑造的人设是:一个家境贫寒、品性不坏、甚至有些才华,
但却对主流奋斗路径感到极度厌倦和疏离的年轻人。一个渴望安宁,
并且可能……需要被拯救的灵魂。时机在一个细雨绵绵的下午成熟。店里没有其他客人,
沈静澜在吧台后擦拭杯子,江屿坐在老位置,面前摊着一本《沉思录》。雨声淅沥,
气氛安静得恰到好处。沈静澜忽然轻轻咳嗽了几声,脸色有些苍白,她用手按了按太阳穴,
身影微微晃了晃。江屿立刻起身,走过去,语气带着真诚的关切:“沈小姐,你没事吧?
脸色看起来不太好。”沈静澜抬起头,有些勉强地笑了笑:“没事,可能有点低血糖,
老毛病了。”江屿没有多问,转身走到吧台,熟门熟路地找到放方糖的罐子,
夹了两颗放进一个干净的杯子,兑了温水,递给她:“先喝点糖水缓一缓。
”他的动作自然流畅,没有丝毫刻意。沈静澜愣了一下,接过杯子,低声道谢。
喝了几口糖水,她的脸色缓和了些。她看着窗外连绵的雨丝,
忽然轻声说:“谢谢你……你好像,总是很安静。”江屿知道,窗口期打开了。他回到座位,
没有立刻接话,而是沉默了片刻,
才用一种带着些许自嘲和疲惫的语气开口:“可能是因为……累了吧。”“累了?
”沈静澜有些好奇。二十岁的年轻人,说出这种饱经沧桑的话,总有些违和。“嗯。
”江屿望着窗外的雨,眼神放空,仿佛在对自己说,“有时候觉得,
很多人都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跑道上拼命奔跑,不敢停,也不敢看旁边的风景。可是,
谁又知道跑道的尽头是什么呢?也许……是另一条更累的跑道吧。”他顿了顿,转向沈静澜,
露出一个苦涩而真诚的微笑:“沈小姐,你看你这间咖啡店就很好,安静,自在。
有时候我真羡慕你,能拥有这样一份与世无争的宁静。”这句话,像一颗精心计算过的石子,
投入了沈静澜心湖的深处。她看着他年轻却写满倦怠的脸庞,
那双眼睛里没有这个年纪该有的野心和光芒,
反而是一种她无比熟悉的……对喧嚣世界的疏离和疲惫。她想起了亡夫,
那个同样年轻却早早在商海搏杀中耗尽心力、最终意外离去的男人。她也曾劝过他停下来,
看看风景,可他总是说,停不下来。那一刻,沈静澜在这个陌生的男大学生身上,
看到了一种诡异的共鸣。一种对“停下来”的共同渴望。雨停了,天边出现一道淡淡的彩虹。
江屿知道,火候差不多了。他起身结账,如同往常一样。但在离开前,他仿佛鼓足了勇气,
对沈静澜说:“沈小姐,如果……如果你店里需要人帮忙打理一下花草,或者有什么力气活,
我可以的。我……我最近时间比较多。”他适时地流露出一点窘迫,但又不过分卑微。
沈静澜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几秒,
似乎是在重新审视这个已经在她店里出现了几个月的年轻人。“好啊。
”她最终轻轻点了点头,语气平和,“后院那几盆花,是该修剪一下了。你明天上午有空吗?
”江屿的心脏,在那一刻,沉稳地跳动了一下。他知道,第一步,成功了。“有空。
”他微笑着,笑容干净,不带一丝杂质。从修剪花草开始,到帮忙整理仓库,
再到偶尔开车接送她去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江屿上辈子有驾照,
重生后很快找机会考了回来,车技娴熟沉稳,江屿以一种缓慢而可靠的速度,
渗透进沈静澜的生活。
行生涯积累的谈资、以及处理琐事时那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和周到多年职场历练的本能,
都让沈静澜感到惊讶和舒适。他从不越界,从不提任何要求,也从不打探她的隐私。
他只是安静地存在,提供着恰到好处的帮助和陪伴。他像一株不需要太多阳光和水分,
却能悄然带来荫凉的植物。更重要的是,他那种对“奋斗”的摒弃,对“躺平”生活的向往,
无形中契合了沈静澜当下的心境。和他相处,让她感到放松,
甚至有一种“同道中人”的错觉。两个月后,沈静澜提出,
她城郊的山顶别墅需要人定期照看,花园很大,她一个人打理不过来。
问江屿愿不愿意搬过去住,算是兼职管家,包吃住,还有一份不错的“薪水”。
江屿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他知道,这不仅仅是省下宿舍费那么简单。
这是通往他理想生活的钥匙。搬家那天,
室友们看着他把简单的行李扔进沈静澜那辆低调但价值不菲的SUV后备箱,眼神复杂,
有羡慕,有鄙夷,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惊。他们终于意识到,
江屿当初那句“找富婆提前退休”,并非玩笑。江屿没有回头。他坐进副驾驶,系好安全带,
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曾经让他感到窒息的城市丛林。车子驶出市区,盘山而上,
空气越来越清新,视野越来越开阔。半山腰的别墅区掩映在浓密的绿荫中,
静谧得如同另一个世界。沈静澜的别墅位于山顶最佳的位置,占地广阔,设计极简现代,
巨大的落地窗外是无敌的山景和城市远景。“你的房间在一楼,带独立卫浴,窗外就是花园。
”沈静澜把钥匙递给他,语气依旧平淡,“这里平时就我们两个人,每周会有钟点工来打扫。
你喜欢安静,应该会适应。”江屿接过钥匙,指尖传来冰凉的金属触感。
他站在空旷奢华的客厅里,看着窗外如画般的风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山间清冽的空气充满肺叶。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从四肢百骸弥漫开来。成了。
他成功地把自己“卖”了出去,卖了一个好价钱——用虚假的脆弱和精心设计的共鸣,
换取了这个真实的、可以让他彻底躺平的避风港。当天晚上,
他睡在比大学宿舍宽敞柔软十倍的大床上,一夜无梦。从此,江屿过上了他梦寐以求的生活。
他不再需要关心股市涨跌,不再需要应付复杂的同事关系,
不再需要为KPI和年终奖绞尽脑汁。他的“工作”很简单:睡到自然醒,
在专业的厨房里给自己做一顿精致的早餐,然后去花园里修剪花草,喂喂池塘里的锦鲤。
下午,可能会在阳光房里看沈静澜收藏的冷门电影,或者开车去山下的湖边钓鱼。晚上,
如果沈静澜有兴致,会和他一起喝点酒,聊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大多数时候,各自安好。
他刻意保持着一种松散而舒适的状态,绝不过分殷勤,也绝不显得懒散。
他把自己打造成这个奢华空间里一个和谐的背景板。沈静澜似乎也很满意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