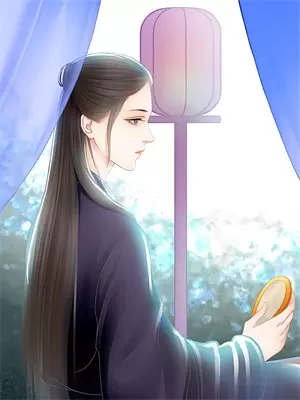奶奶临终前塞给我一把缠着红线的铜钥匙:“孙儿,七日后子时,去老宅祠堂,
打开那只檀木箱……”“记住,无论看到什么,都别相信。”我本以为只是老人家的糊涂话。
头七那晚,我拿着钥匙踏入尘封的祠堂。檀木箱里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嫁衣,鲜红如血。
而嫁衣下面,压着一本泛黄的族谱——我的名字,
赫然写在百年前一个溺亡女子的丈夫那一栏。窗外忽然传来唢呐声,
我回头一看——一顶大红花轿正停在院子里,轿帘微动,一只湿漉漉的手正缓缓伸出来。
---第一章 归乡陈默接到父亲电话时,
正在城市逼仄的出租屋里修改一份永远也改不完的设计图。“小默,
奶奶……恐怕就这两天了。”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那头显得异常疲惫,
还带着一种陈默难以理解的沉重,“你请假回来一趟吧,有些事情……必须你在场。
”电话里有短暂的沉默,只有电流的滋滋声。“爸?”陈默停下敲击键盘的手,
心里莫名一沉。他和奶奶不算特别亲近,童年记忆里,
奶奶总是沉默地坐在老家那座昏暗堂屋的藤椅上,眼神望向门外,仿佛在等待什么。
但血脉相连的感应,还是让他心头泛起酸楚。“回来再说吧。”父亲最终只是叹了口气,
“尽快。”挂了电话,陈默看着电脑屏幕上扭曲的设计线条,忽然觉得一阵心烦意乱。
窗外是都市永不熄灭的霓虹,而父亲电话里带来的,
却是来自那个偏远古旧水乡的、带着潮湿霉气的召唤。他请了假,第二天一早就踏上了归途。
火车换大巴,大巴换三轮,一路颠簸,窗外的景色从高楼林立逐渐变为田野平畴,
最后是交错纵横的河网。空气也变得粘稠湿润,
带着水乡特有的、植物和水汽腐烂混合的气息。他的老家,清水镇,
是一座陷落在庞大水泽深处的古老镇落。镇子被无数条大小河道切割得支离破碎,
出行全靠乌篷船和几座年代久远的石桥。据说,镇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清,甚至更早,
祖上曾靠漕运显赫一时,但如今早已没落,只剩下些不愿离开的老人和破败的老宅。
陈默记得小时候回来,最怕的就是镇口那条宽阔而湍急的清水河,
于河里的种种传说——拉人脚踝的水鬼、夜半唱歌的河漂子、还有那座据说拜了就能保平安,
却总是阴森森的河神庙。船夫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头,撑着长篙,乌篷船破开墨绿色的水面,
悄无声息地滑入镇子。两岸是斑驳的石灰墙,浸水的青石板台阶长满滑腻的青苔,
一些歪斜的老树将枝桠探入水中,形如鬼爪。整个镇子安静得可怕,几乎听不到人声,
只有船桨划破水面的哗啦声,以及风穿过空荡巷弄的呜咽。“后生,不是本地人吧?
”船夫忽然开口,声音沙哑,打破了沉寂。“我回来看我奶奶。”陈默回答。
船夫动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瞥了陈默一眼,
那眼神有些古怪:“陈家阿婆啊……这时候回来,也好,也好。”他没再说什么,
但陈默心里那点不安却逐渐放大。他注意到,沿途一些临水的窗戶后面,
似乎有目光在窥视他,等他看过去时,又迅速消失。陈家老宅在镇子最深处,
紧挨着那片被称为“沉尸荡”的广阔芦苇荡。据说那里水深莫测,连通着地下暗河,
每年都有意外甚至非意外的人沉尸其中。老宅比陈默记忆中更加破败,黑瓦白墙剥落严重,
露出里面暗沉的木质结构,像一头疲惫的、匍匐在水边的巨兽。父亲陈建国等在门口,
才五十出头的人,两鬓已斑白,脸上刻满了忧虑的皱纹。“回来了。
”他接过陈默简单的行李,声音低沉,“奶奶一直撑着等你。
”宅子里弥漫着浓重的草药味和老人身上特有的衰败气息。奶奶躺在床上,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皮肤蜡黄,紧紧包裹着骨架。她闭着眼,呼吸微弱。“妈,
小默回来了。”陈建国俯下身,轻声说。奶奶的眼皮颤动了几下,艰难地睁开一条缝。
她的眼神原本已经涣散,但在看到陈默的瞬间,骤然爆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是惊恐,
是焦急,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她枯瘦的手猛地从被子里伸出,
死死抓住陈默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冰凉的触感让陈默打了个寒颤。
“钥……钥匙……”她的嘴唇哆嗦着,吐出模糊不清的音节。陈建国脸色微变,似乎想阻止,
但奶奶已经用尽力气,将一件硬物塞进了陈默手里。那是一把古旧的黄铜钥匙,
上面密密麻麻地缠着暗红色的丝线,那红色红得有些不正常,像凝固的血。
“孙儿……听好……”奶奶的眼睛死死盯着陈默,仿佛要将每一个字刻进他的灵魂,
“七日后……子时……去祠堂……打开……东墙根……那只檀木箱……”她剧烈地喘息着,
胸腔像破风箱一样起伏。“记住!记住!”她的指甲几乎要掐进陈默的肉里,
“无论……无论看到什么……都别信!别回头!别答应!”说完这几句话,
她像是耗尽了所有力气,手一松,瘫软下去,眼神重新变得空洞,只有嘴唇还在无声地翕动,
反复念叨着两个字,
默凑近了才听清——“……水……娘……”陈默握着那把冰凉刺骨、缠着诡异红线的铜钥匙,
看着床上气若游丝的奶奶,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七日?子时?祠堂?檀木箱?别信?
别回头?别答应?水娘?这都什么跟什么?他困惑地看向父亲,却见陈建国脸色煞白,
嘴唇紧抿,眼神躲闪,最终只是沉重地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
那种被无形之物窥视、被拖入某个巨大阴谋漩涡的感觉,再次将陈默紧紧包裹。
奶奶在第二天凌晨咽了气。葬礼按照清水镇的旧俗进行,繁琐而压抑。整个过程,
陈建国都显得心事重重,时常望着那片阴森的“沉尸荡”出神。
前来吊唁的镇民们也透着古怪,他们送上奠仪,说些节哀顺变的客套话,但看陈默的眼神,
总带着一种隐秘的探究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怜悯?
陈默试图询问关于奶奶遗言、关于祠堂、关于“水娘”的事情,
但无论是父亲还是镇上的老人,都讳莫如深,要么岔开话题,要么直接沉默。
时间在哀乐和香火味中流逝,很快就到了头七的前夜。第二章 禁忌头七,回魂夜。
按照清水镇的规矩,这一夜,逝者的魂魄会返回生前居所,做最后的告别。
亲人们需要备好酒菜,焚香祷告,然后回避,留出空间给魂魄,绝不能冲撞。但奶奶的遗言,
却明确要求陈默在头七子时,去往一个更加禁忌的地方——陈家祠堂。
陈家祠堂位于老宅的最深处,单独的一个院落,据说比老宅本身的历史还要悠久。
陈默小时候曾被严厉告诫,绝对不许靠近那里。那里面供奉的,不仅仅是陈家的列祖列宗,
还有一些……别的、不干净的东西。这是镇上小孩间口耳相传的隐秘。晚饭时,
气氛格外凝重。陈建国喝了几杯闷酒,看着窗外彻底暗下来的天色,
以及天边那轮被薄云遮挡、泛着毛边的月亮,终于开了口。“小默,”他的声音带着酒意,
更显沙哑,“明天……你就回城里去吧。”陈默一愣:“爸,
奶奶头七还没过……”“过了今晚就走!”陈建国的语气突然变得激动,他抓住陈默的手,
眼神里带着恳求,甚至是一丝恐惧,“听爸的话,忘了你奶奶说的话!忘了那把钥匙!
永远别再回来!”“为什么?”陈默不解,同时心里那股叛逆和探究欲也被勾了起来,
“奶奶到底让我去祠堂干什么?檀木箱里有什么?‘水娘’又是什么?”“别问!
”陈建国猛地打断他,脸色在昏暗的灯光下显得有些狰狞,“那都是老一辈的糊涂事!
是封建迷信!是……是诅咒!你沾上了,就甩不掉了!”“诅咒?”陈默的心跳漏了一拍。
陈建国似乎意识到自己失言,颓然地松开手,又灌了一口酒,喃喃道:“总之,
你不能去……不能去祠堂……尤其是今晚……”他反复念叨着,眼神涣散,
仿佛陷入了某种可怕的回忆。看着父亲这副模样,陈默心中的疑虑和不安达到了顶点。
奶奶临终前诡异的嘱托,父亲反常的恐惧和阻拦,镇上人古怪的眼神,
还有那把缠着血红色丝线、触手冰凉的铜钥匙……所有的一切,都指向祠堂,
指向那个檀木箱。那里一定隐藏着陈家,乃至整个清水镇的秘密。一个关于“水娘”,
关于诅咒的秘密。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的心脏,但另一种力量——或许是血脉里的牵连,
或许是对真相的渴望,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的牵引——却推着他,走向那个禁忌之地。
他摸了摸口袋里那把冰冷的钥匙,它仿佛带着奶奶最后的意志。去,还是不去?夜色渐深,
虫鸣唧唧,远处芦苇荡的方向,传来若有若无的水流声,像是某种低语。子时快到了。
陈默最终做出了决定。他无法对奶奶的遗言视若无睹,也无法在巨大的谜团前转身离开。
他要知道真相。他借口累了要休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父亲还在堂屋喝着闷酒,
眼神已经有些迷离。等到外面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父亲隐约的鼾声传来时,陈默深吸一口气,
轻轻推开房门,拿着早已准备好的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向老宅最深处的那个院落。
祠堂的院门是一扇沉重的、黑漆剥落的木门,上面挂着一把同样古老的大铜锁。
锁上同样缠着暗红色的丝线,只是年代更为久远,颜色近乎黑紫。院子里杂草丛生,
在惨淡的月光下投下幢幢鬼影。正对着院门的,就是陈家祠堂。
那是一座更加古旧的黑瓦建筑,飞檐翘角,在夜色中如同蹲伏的怪兽。窗户被木板钉死,
缝隙里透出深不见底的黑暗。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香火残留味和木头腐朽的气息,
还有一种……淡淡的、水腥气。陈默的心脏在胸腔里狂跳,手心里全是冷汗。
他走到祠堂门前,那扇门比他想象的还要沉重。他掏出那把缠着红线的铜钥匙,插入锁孔。
“咔哒。”一声轻响,在死寂的夜里显得格外清晰。铜锁应声而开。他深吸一口气,
用力推开了祠堂的门。“吱呀——呀——”令人牙酸的摩擦声拖得很长,
仿佛开启了某个尘封的禁忌。一股混合着陈年霉味、香灰味和那股若有若无水腥气的阴风,
从门内扑面而出,激得陈默连打了几个寒噤。手电光柱刺入黑暗,照亮了祠堂内部的景象。
第三章 祠堂深处祠堂内部比从外面看感觉更加空旷、高深。手电光柱扫过,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密密麻麻、层层叠叠的牌位,整齐地排列在正前方的神龛之上,
从高处俯瞰着下方,像无数双沉默的眼睛。牌位上的字迹在光线下模糊不清,
但那种积年累月的肃穆和阴森,却沉甸甸地压下来。空气中漂浮着细小的尘埃,
在手电光中疯狂舞动。地面是巨大的青石板,缝隙里长着顽强的苔藓,湿滑粘腻。
陈默按照奶奶的指示,将光柱移向东墙根。那里果然摆放着一只箱子。不是普通的木箱,
而是一只色泽沉黯、雕刻着繁复缠枝莲纹路的檀木箱。箱子不大,约莫半人高,
箱体上同样缠绕着那种暗红色的丝线,密密麻麻,几乎将整个箱子包裹起来,
像是在束缚着什么。箱扣是一把造型奇特的铜锁,锁孔的形状,正好与陈默手中的钥匙吻合。
除此之外,祠堂里再无他物。没有想象中的恐怖景象,
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和无处不在的陈旧感。陈默走到檀木箱前,蹲下身。离得近了,
那股淡淡的水腥气似乎更明显了一些,仿佛这箱子是从水底捞出来的一般。
箱子上雕刻的莲花纹路,在电筒光下显得异常清晰,花瓣舒展,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妖异。
他再次掏出那把铜钥匙。钥匙触手冰凉,上面的红线在昏暗光线下,
仿佛有暗红色的流光转动。“无论看到什么,都别相信。”奶奶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
他深吸一口气,将钥匙插入锁孔。转动。“咔。”铜锁弹开。陈默的手有些颤抖,
他轻轻拂开那些缠绕的红线——那些线入手竟也有些潮湿阴冷——然后,揭开了箱盖。
一股更浓烈的、混合着檀香、霉味和水腥气的怪异气味涌出。箱子里面,没有金银财宝,
没有骸骨尸身,也没有预想中的妖魔邪祟。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刺目的红。
那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嫁衣。真正的凤冠霞帔,大红绸缎的料子,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
也鲜红得如同刚刚浸染过鲜血。上面用金线银线绣着精致的龙凤呈祥图案,针脚细密,
华美非常。但这份华美,在此刻此地,却显得无比诡异、悚然。一件嫁衣?
为什么会藏在祠堂的箱子里?还被红线缠绕封锁?陈默强忍着心头的悸动,
小心翼翼地将那件嫁衣捧了出来。嫁衣入手沉重,布料冰凉丝滑,仿佛真丝的质感,
却又带着一种异常的湿气。嫁衣下面,压着几本线装的、纸张泛黄脆化的册子。最上面一本,
封面上用古朴的毛笔字写着《陈氏宗谱》。族谱?陈默心中一动,似乎抓住了什么线索。
他拿起那本族谱,借着电筒光,小心翼翼地翻看起来。
族谱记录着陈氏一族绵延数百年的血脉传承,生卒嫁娶,一一在列。他一页页地往后翻,
目光掠过那些陌生的名字和年代,直到接近末尾……他的动作猛地顿住!瞳孔骤然收缩!
在记载着“民国七年”的那一页,
他看到了一段让他血液几乎冻结的文字:“陈公讳明远光绪廿一年生……配柳氏,
讳如玉光绪廿四年生,民国七年六月十五溺毙于沉尸荡……”这没什么,祖上有人溺亡,
虽不祥,但也并非不可能。让他浑身冰凉的,是旁边用稍小字体标注的补充记录,
以及旁边一个显然是很久以后才强行添加上去的名字!那条补充记录写着:“柳氏如玉,
乃奉祀‘水娘’之选,不幸早夭,然婚约已定,阴契已成,夫陈明远誓不另娶,以全其节。
”而旁边那个被朱笔狠狠划掉,却又依稀可辨、墨色较新的名字,赫然是——陈默!
他的名字,被写在“夫陈明远”这个位置旁边!像是某种替代,某种……继承?民国七年?
那是一百多年前!陈明远是他曾祖辈的名字!而他陈默,一个活在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人,
名字怎么会出现在百年前一个溺亡女子的“丈夫”这一栏?阴契?奉祀水娘?
“水娘”……奶奶临终前念叨的,就是这个!一股无法形容的寒意瞬间席卷了陈默的全身,
他感觉自己的头皮都要炸开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恐怖故事,
这似乎是一个延续了百年的、与他血脉相连的诅咒!就在他心神俱震,
那——“呜哩哇——呜哩哇——”一阵极其突兀、尖锐、喜庆中透着无比凄厉诡异的唢呐声,
毫无征兆地,从祠堂外面传了进来!这乐声是如此之近,仿佛就在院门之外!是迎亲的乐曲!
陈默浑身的汗毛瞬间倒竖!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他猛地回头,
透过祠堂洞开的大门,望向院子——只见惨淡的月光下,院门不知何时已然洞开。
一顶大红色的、装饰着繁复金线绣花的花轿,正静悄悄地、端端正正地停在院子中央。
轿帘低垂,纹丝不动。四周空无一人,只有那顶轿子,和那依旧在夜空中凄厉回响的唢呐声,
构成了一幅无比邪异、令人窒息的画面。陈默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彻底凝固,大脑一片空白。
奶奶的警告在耳边疯狂回响:“无论看到什么,都别信!别回头!别答应!”然后,
他最恐惧的事情发生了。那顶静止的花轿,轿帘微微动了一下。不是被风吹动,而是从里面,
被一只……手,轻轻拨开了一道缝隙。那只手,苍白、浮肿,
皮肤因为长时间浸泡而显得皱巴巴的,指甲缝里嵌着暗绿色的水藻。
湿漉漉的袖子紧贴着手臂,往下滴落着浑浊的水珠,落在轿前的青石板上,
发出“嗒……嗒……”的轻响。那只手缓缓地、缓缓地从轿帘缝隙中伸了出来,
朝着祠堂的方向,朝着僵立在内的陈默,做了一个极其轻柔,
却又无比清晰的——招手的动作。那只湿漉漉的手,在惨淡月光下泛着死寂的灰白,
指尖微勾,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意味。水滴顺着皱缩的皮肤滑落,
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圈一小圈深色的水渍。嗒。嗒。声音很轻,却像重锤敲在陈默的心上。
他全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大脑一片空白,
只剩下奶奶嘶哑的警告在颅内疯狂回荡:“别信!别回头!别答应!”唢呐声不知何时停了,
死寂重新笼罩下来,比之前更加沉重,压得人喘不过气。院子里,
只有那顶孤零零的大红花轿,和轿帘缝隙后那只持续招手的、来自水底的手。跑!
这个念头如同本能般炸开。陈默猛地转身,甚至来不及合上檀木箱,
也顾不上那本掉落在旁的族谱,像只受惊的兔子,跌跌撞撞地冲向祠堂门口!
他不敢再看那只手,不敢再看那顶轿子,只想立刻逃离这个鬼地方!逃离这个被诅咒的祠堂,
逃离这个诡异的镇子!冲出祠堂院门的那一刻,他几乎是手脚并用地扑向老宅主屋的方向。
身后的黑暗仿佛有生命般粘稠,紧紧追摄着他。他总觉得,那只湿冷的手,
下一刻就会搭上他的肩膀。“砰!”他重重撞开老宅堂屋的门,反手死死闩上,
背靠着门板剧烈喘息,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跳出来。堂屋里一片漆黑,
父亲房间的方向传来沉重的鼾声,对刚刚发生在咫尺之遥的恐怖一幕毫无所觉。
安全了……暂时。他滑坐在地上,冷汗浸透了后背,四肢冰凉发软。黑暗中,
他死死盯着那扇被他闩上的门,生怕下一秒,门板就会被什么东西敲响,或者,
一只湿漉漉的手会从门缝里伸进来。那一夜,陈默几乎没合眼。
何一点细微的声响——风声、虫鸣、甚至是老宅木结构自然的收缩声——都能让他惊跳起来。
那只苍白浮肿的手和那顶静默的花轿,如同烙印,深深刻在他的脑海里。天亮时分,
父亲陈建国推门出来,看到蜷缩在门后、眼窝深陷、脸色苍白的陈默,吓了一跳。“小默?
你……你昨晚没睡?”陈建国的声音带着宿醉的沙哑,但眼神里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陈默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父亲,声音干涩:“爸,我昨晚……去祠堂了。
”陈建国的脸色“唰”地一下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我看到了,
”陈默继续说着,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族谱上,我的名字,
写在那个淹死的柳如玉旁边。还有……花轿,院子里停了顶花轿,
里面……里面有只手伸出来……”“别说了!”陈建国猛地打断他,冲过来抓住他的肩膀,
力气大得吓人,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愤怒,“我让你别去!
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那到底是什么?!‘水娘’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我的名字会在上面?!”陈默也激动起来,反抓住父亲的手臂,“告诉我!
我有权知道!”陈建国看着儿子激动而恐惧的脸,抓住他肩膀的手渐渐无力地滑落。
他颓然地后退两步,靠在冰冷的墙壁上,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
“是诅咒……是我们陈家……不,是整个清水镇,欠下的债……”他喃喃着,
眼神空洞地望着虚空,仿佛看到了遥远的过去。“一百多年前,镇上大旱,河水干涸,
田地龟裂。当时的族长,也就是我们的高祖,听信了一个游方道士的话,
说……说只要向河神献上一位纯洁的处女作为‘水娘’,便能求得甘霖。
”“他们选中了柳家的女儿,柳如玉。那姑娘……才十六岁,据说长得极美,性子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