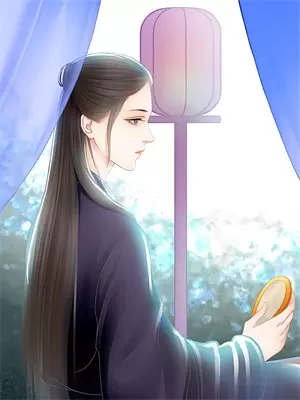回村第一天,奶奶就叮嘱我三件事:别碰村口的石狮子,别吃供桌上的糯米糕,
别答应半夜门外叫你名字的声音。我一一照做,平安度过了七天。第七天夜里,
我听到妈妈在门外哭:闺女,开门啊,妈妈脚扭了。我刚要冲出去,
却收到奶奶的短信:傻孩子,你妈十五年前就死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了。一人在老家,
刚下大巴。你可能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在北上广 996 了三年的社畜,
被一纸奶奶病重的电报催回这个地图上都快找不到名字的山村时,心里是什么滋味。
颠簸了整整六个小时的盘山土路,骨头都快散架了。看着窗外越来越稀疏的灯火,
和手机信号格一点点彻底消失,我这心里,除了对奶奶的担忧,
就只剩下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憋闷。我们村叫石坨村,藏在深山老林里,
闭塞得像是被时间遗忘了一样。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比我奶奶的年纪都大,
枝桠张牙舞爪地伸向天空,像一把巨大的、不祥的伞。到家时,天已经擦黑。
奶奶比我想象中要好些,虽然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但眼神还算清亮。看到我,
她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随即又被更深的忧虑覆盖。她挥挥手,
示意我关上她那间老屋的房门。木门发出吱呀一声呻吟,像是疲惫的叹息。屋子里很暗,
只有一盏煤油灯摇曳着微弱的光晕,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张牙舞爪的。奶奶攥着我的手,她的手心粗糙得像老树皮,冰凉一片。她压低了声音,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囡囡,你回来了就好。听着,在村里住着,
有三件事,你务必记牢,一步都不能错!她的眼神太过严肃,
甚至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恐惧,让我也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屏住了呼吸。第一,绝对,
绝对不能碰村口那对石狮子!尤其是右边那只缺了半只耳朵的,看都不要多看!
村口的石狮子?我努力回想,好像是有那么一对,布满青苔,残破不堪,蹲在老槐树下,
像两个沉默的鬼魅。第二,不管谁家办事,还是祠堂上了供,那供桌上的糯米糕,
一口都不能吃!闻都别闻!我心里嘀咕,这算什么规矩?
小时候好像还偷吃过祠堂的供果来着,也没什么事啊。第三,奶奶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几乎成了气音,混着窗外呜咽的风声,钻进我的耳朵,晚上,特别是子时前后,
要是听见门外有人叫你的名字,清清楚楚地叫你的大名,千万别应声!更别开门去看!
听见没?我后背有点发凉,但还是点了点头:奶奶,这都什么年代了……
别管什么年代!奶奶猛地打断我,手指用力掐得我生疼,这七天,你就在家陪着我,
哪儿也别去,天黑了就锁好门,谁叫都别开!平平安安过了这七天,你就赶紧买票回城里去!
二头三天,风平浪静。我每天守着奶奶,给她熬药,做饭,陪她说说话。
信号时有时无,刷个朋友圈都费劲,日子过得仿佛倒退了几十年。我谨记着奶奶的嘱咐,
没去碰那石狮子,虽然每次路过村口,总觉得那缺耳石狮的空洞眼窝,似乎在盯着我。
供桌倒是没见过,村里似乎也没谁家办红白喜事。至于半夜叫名字?更是没影儿的事。
山村的夜,静得吓人,只有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各种不知名的虫鸣。然而,第四天开始,
事情有点不对劲了。那天晚上,我睡得正沉,忽然被一阵若有若无的哭声惊醒了。
那哭声……是个女人的。飘飘忽忽,断断续续,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
又像是就在我家窗根底下。尖细,凄婉,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寒意,直往你骨头缝里钻。
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哭声又没了。只有风声。第五天,第六天,一模一样。总是在后半夜,
那女人的哭声准时响起,而且……似乎一天比一天清晰,一天比一天靠近。到了第六天晚上,
我甚至能分辨出,那哭声里好像还夹杂着模糊不清的字句,像是在呼唤什么。我心里发毛,
跑去问奶奶。奶奶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着,只是反复念叨:别听!捂上耳朵!
睡你的觉!就当没听见!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害怕。
那种弥漫在老屋和整个村子的诡异氛围,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三第七天,终于来了。
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感觉村里仅剩的几户人家今天都关门闭户,安静得异乎寻常。
连平时满村乱窜的土狗都不见了踪影。空气黏稠得像是胶水,
带着一股陈年霉味和香烛纸钱混合的怪味。奶奶一整天都坐立不安,眼神时不时飘向窗外,
手里攥着一串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佛珠,手指神经质地捻着。天黑得特别快。
我早早锁死了门窗,检查了好几遍。奶奶已经睡下了,我却毫无睡意,坐在堂屋的椅子上,
心脏跳得像打鼓。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当桌上的老式座钟时针颤巍巍地指向11时,
那哭声,又来了。这一次,它不再飘忽,而是无比清晰地萦绕在我家门外!而且,
那声音……囡囡……开开门啊……囡囡……我浑身一僵,血都凉了半截。
这声音……为什么那么像……我妈妈?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
据说是受不了这穷山沟,跟一个外乡人跑了。这么多年,音讯全无。我对她的印象,
早已模糊。可门外这哭声,这呼唤,却与我记忆深处那个温柔又带着哀愁的声音,
一点点重合起来。囡囡……是妈妈啊……妈妈回来了……开门让妈妈看看你……
着痛苦的抽气声:妈妈……妈妈不小心把脚扭了……好疼啊……站不住了……你快开开门,
扶妈妈一把……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是我妈?她真的回来了?她受伤了?
就在门外?十五年了……我对她有过怨恨,但更多的,是藏在心底的思念。
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就要往门口冲。
手指几乎要触碰到那冰冷的门闩——就在这一刹那!我放在桌上的手机屏幕,
突然毫无征兆地亮了起来,发出刺眼的幽蓝光芒!这深山老林,不是早就没信号了吗?
我下意识地低头一看。是一条短信。发送人,赫然显示着——奶奶!而短信的内容,
只有短短一行字,像一把冰冷的匕首,瞬间刺穿了我的心脏:傻孩子,
你妈十五年前就死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了。四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
我伸向门闩的手僵在半空,指尖冰凉。堂屋里,只有那座老钟发出单调而沉重的滴答声,
一下,一下,敲击着我的耳膜。门外的哭声还在继续,
甚至带上了几分急促和哀切:囡囡……快开门啊……妈妈脚好痛……外面好冷……
可这声音,此刻听在我耳里,却再也没有半分温情,只剩下彻骨的阴寒和毛骨悚然的诡异。
我猛地扭头,看向里屋奶奶的床铺。床上空空如也!奶奶不见了!她刚才明明睡下了!
一个病重的老人,能去哪里?那……这条短信……我手指颤抖着,死死攥着手机,
那屏幕上的字像烧红的烙铁,烫着我的眼睛。傻孩子,
你妈十五年前就死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了。
供桌上的糯米糕……半夜叫名字的声音……奶奶严肃到近乎恐惧的叮嘱……还有这连续三夜,
越来越近的哭声……所有支离破碎的线索,在这一刻,被这条来自奶奶的短信,
串成了一条冰冷黏滑的毒蛇,瞬间缠紧了我的心脏,让我几乎窒息。咚……咚……咚……
不是钟声。是敲门声。很轻,很缓,却带着一种不依不饶的执拗。门外的妈妈
停止了哭泣,声音变得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诡异的温柔:囡囡,
你都长这么大了……开门,让妈妈好好看看你……她的声音,几乎就贴在了门板上,
隔着一层薄薄的木板,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正把脸贴在门缝上,朝着里面窥视的样子。
我屏住呼吸,一步步,一步步地往后挪,后背紧紧贴住了冰冷的土墙,冷汗已经浸透了内衣。
手机屏幕又闪了一下。一条新的短信,再次来自奶奶:它在骗你。千万别看它的眼睛。
它?谁是它?我头皮瞬间炸开!全身的汗毛倒竖!几乎是同时——哗啦……哗啦……
窗户的方向传来了轻微的刮擦声。我家的窗户,是老式的木棂窗,糊着报纸。此刻,
借着堂屋煤油灯微弱的光,我清晰地看到,窗户纸上,正被什么东西,从外面,一下,
一下地……刮擦着。那动作,缓慢而充满恶意。紧接着,一只眼睛,
猛地贴在了刚刚被刮薄的那一小块窗纸上!浑浊,布满血丝,瞳孔缩得像针尖一样小。
它就那样,一动不动地,透过那小小的缝隙,死死地盯着堂屋里的我!门外,是妈妈
温柔到恐怖的呼唤和坚持不懈的敲门声。窗外,是那只无法形容的、充满恶意的眼睛。
而我的手机,还攥在汗湿的手里,屏幕上是那两条来自未知奶奶的、救命的,
却又将恐怖推向极致的短信。奶奶在哪里?门外窗外的,又到底是什么东西?那石狮子,
那糯米糕,又藏着怎样的秘密?我感觉自己的神经已经绷到了极限,仿佛下一秒就要断裂。
就在这时,敲门声和刮擦声同时停止了。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下来。然后,
我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是奶奶的声音。但这一次,她的声音不是从里屋,
也不是从手机里传出。而是……从门外,和那个妈妈的声音重叠在了一起,
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冰冷的笑意,轻轻地说:囡囡,糯米糕……好吃吗?
五糯米糕……这三个字像三根冰锥,狠狠扎进我的脑海。我什么时候吃过糯米糕?
记忆疯狂倒带,最终定格在回村第二天下午。邻居李婶端来一块雪白的糕点,
说是自家新打的,给奶奶尝尝鲜。奶奶当时睡着了,我推辞不过,又确实饿了,
就在灶房偷偷掰了一小块……那糯米糕软糯清甜,
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类似檀香的味道……我吃了!我违反了奶奶的第二条禁忌!
冷汗瞬间浸透全身,四肢百骸像是被瞬间抽干了力气,顺着墙壁软软滑坐到地上。原来,
从那一刻起,我就已经踏入了陷阱?所以这哭声才能一天天精准地找到我,靠近我?
门外的奶奶和妈妈的声音依旧重叠着,带着那股冰冷笑意,
还在继续:吃了就好……吃了,就是自己人了……囡囡,
开门吧……让奶奶妈妈进来……它们的声音开始变得同步,不再区分彼此,
融合成一种非男非女、不似活物的怪异腔调,不断重复着开门的催促。
窗户上那只眼睛依旧死死盯着我,瞳孔在微弱的光线下,似乎微微转动着,
锁定了我瘫坐的位置。恐惧像无数细密的虫子,啃噬着我的理智。我死死捂住嘴巴,
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屏住了,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跳出来。
手机屏幕又亮了。还是奶奶:它在用我的声音。别信。去灶房,锅底灰,
抹在门缝和眼皮上。快!灶房?锅底灰?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冲向与堂屋相连的灶房。农村的老式土灶,常年烧柴,
锅底积着厚厚一层黑色的灰烬。我顾不得脏,伸手胡乱抹了一大把,触手是冰凉的粗糙感。
按照短信指示,我跌跌撞撞冲回堂屋,先将一把锅底灰死死按在门缝上,
然后又胡乱地将黑灰抹在自己的眼皮上。世界瞬间暗了一层。
也就在锅底灰覆盖上门缝的刹那,门外那催命般的开门声,猛地停顿了一下,
随即变成了一种被激怒的、尖锐的嘶鸣!嘶——你敢——!与此同时,
窗户上那只眼睛像是被烫到一般,猛地缩了回去,窗外传来一声压抑的、充满恶意的低吼。
有用!这锅底灰真的有用!我靠着门板,大口喘着粗气,
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更深的恐惧交织在一起。手机再次震动,
屏幕在昏暗的光线下格外醒目:它们暂时进不来。但灰撑不了多久。听着,要想活命,
必须去村口,把右边那缺耳石狮子底下压着的东西挖出来。去村口?现在?
外面不知道有多少那种东西在游荡!而且,要动那绝对不能碰的石狮子?没有别的路了。
它用糯米糕标记了你,用叫魂诱你应答,你身上『人』的气味已经快散了。
只有那东西能救你。记住,无论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都不能回头!拿到东西后,立刻回来,
把它埋在院子正中央。短信到此为止,无论我怎么回拨,怎么尝试发送信息,
都如同石沉大海。我看着屏幕上冰冷的文字,又看向紧闭的房门和窗户。门外,
那种尖锐的嘶鸣已经变成了低沉的、仿佛无数人在一起的窃窃私语,密密麻麻,
不断冲击着门板。窗户纸上,虽然看不到那只眼睛了,但隐约有几个模糊的黑影在晃动。
留在屋里,等锅底灰失效,必死无疑。出去,按照这神秘短信的指示搏一把,
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我咬紧牙关,一股狠劲从心底冒了出来。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了!
我再次冲进灶房,将锅底灰不要钱似的往自己脸上、脖子上、手臂上所有裸露的皮肤上抹,
直到自己看起来像个黑人。又找到一把生锈但沉重的柴刀,紧紧攥在手里。深吸一口气,
我猛地拉开了堂屋的门栓。六门外,空无一人。只有浓郁得化不开的黑暗,
和一股仿佛实质般的阴冷气息扑面而来,激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村里的夜晚,静得可怕。
不是那种安宁的静谧,而是死寂,仿佛所有的声音,连风声和虫鸣,都被这黑暗吞噬了。
我握紧柴刀,凭借着记忆,深一脚浅一脚地朝着村口的方向摸去。
脸上、眼皮上的锅底灰传来冰凉的触感,这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路两旁的房屋,
全都黑灯瞎火,像一座座沉默的坟墓。有些院门虚掩着,黑洞洞的门缝里,
似乎有东西在窥视。我不敢细看,只能加快脚步。越靠近村口,那股阴冷的气息就越重。
老槐树的轮廓在黑暗中显现出来,像一头匍匐的巨兽。那对石狮子就蹲在树下,
在惨淡的月光下,泛着青惨惨的光泽。右边那只,缺了半只耳朵,格外醒目。
它的眼窝空洞地望着我所在的方向,嘴角似乎……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残酷的笑意?
我强迫自己移开目光,走到它面前。它底座下的泥土,看起来和周围并无不同,
只是格外潮湿,散发着一股土腥味和……淡淡的腐臭味。丢开柴刀,我跪在地上,
用双手开始挖掘。泥土冰冷粘腻,指甲很快翻起,渗出血丝,但我顾不上了。
恐惧和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我,疯狂地向下挖。挖了大概一尺深,我的指尖触碰到了一个硬物。
不是石头,触感更光滑,像是……木头?我心中一动,加快速度,
小心翼翼地将周围的泥土扒开。
那东西渐渐显露出来——是一个长方形的、巴掌大小的、暗红色的木盒子。
盒子表面刻着一些扭曲的、看不懂的符文,入手冰凉刺骨,仿佛握着一块寒冰。
就在我拿起盒子的瞬间!呼——一阵强烈的阴风毫无征兆地刮起,吹得老槐树枝叶狂舞,
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音。我的后背、颈后感受到了一阵刺骨的寒意。
一个声音贴在我耳边响了起来,带着哭腔,是我妈妈
的声音:囡囡……你拿它干什么……快放下……跟妈妈回家……几乎是同时,
另一个方向响起了奶奶焦急的声音:孩子!别信那盒子!那是祸根!快把它埋回去!
到奶奶这儿来!两个声音从不同的方向传来,充满了诱惑与焦急。
我想起短信的叮嘱——不能回头!我死死咬着牙,将木盒子紧紧抱在怀里,站起身,
头也不回地朝着来路,朝着奶奶家的方向发足狂奔!身后的声音瞬间变了调,
从诱惑变成了凄厉的尖叫和诅咒,混杂着仿佛野兽般的咆哮,紧追不舍。
阴风像无数只冰冷的手,撕扯着我的衣服和头发。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就在我身后,
贴得很近,很近……我甚至能闻到那股浓郁的、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和檀香味混合的气息。
我不敢回头,拼命地跑,肺部火辣辣地疼,心脏快要炸开。终于,
奶奶家那熟悉的院门轮廓出现在了前方。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冲了过去,
几乎是撞开了虚掩的院门,反手死死关上,然后将怀里那个冰冷的木盒子按在地上,
用颤抖的手,就在院子正中央,疯狂地刨开泥土,将它埋了进去。
当最后一捧土覆盖上去的刹那。身后所有的声音、追逐感、冰冷的触感,瞬间消失了。
万籁俱寂。只有我粗重的喘息声,在死寂的院子里回荡。我瘫软在地,浑身脱力,
汗水混合着锅底灰,让我看起来狼狈不堪。结束了吗?我……活下来了?我抬起头,
看向奶奶居住的堂屋。那里,不知何时,竟然亮起了昏黄的煤油灯光。一个佝偻的身影,
拄着拐杖,静静地站在门口,无声地看着我。是奶奶。她的脸,在跳动的灯光下,一半明,
一半暗。看不清楚表情。七我瘫坐在冰冷的泥地上,汗水、泥污和锅底灰糊了满脸,
心脏还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冲破喉咙。劫后余生的虚脱感和更深的不安交织在一起,
像两条冰冷的蛇,缠得我透不过气。结束了……吗?堂屋门口,
奶奶的身影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像一个剪影,一动不动。
光线只照亮了她佝偻的下半身和那根磨得光滑的拐杖,她的脸藏在门内的阴影中,看不真切。
奶……奶奶?我的声音干涩沙哑,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她没有立刻回答。
院子里死寂得可怕,连之前一直呜咽的风声都停了。只有埋下木盒的那片新土,
散发着淡淡的土腥味和一丝若有若无的、从盒子上带来的冰冷腐朽气息。几秒钟后,
奶奶的身影动了一下,她拄着拐杖,慢慢地,一步一顿地,从堂屋的门槛里迈了出来。
煤油灯的光终于照亮了她的脸。蜡黄,布满深刻的皱纹,
眼神……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浑浊和疲惫,深处似乎还藏着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
像是愧疚,又像是……解脱?她走到我面前,没有伸手扶我,
只是低头看着那片刚被翻动过的泥土,看了很久很久。挖出来了?她终于开口,
声音苍老得像是被风沙磨过无数次。我点了点头,喉咙发紧,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想问她去了哪里,想问那短信是不是她发的,想问门外窗外的到底是什么,
想问这木盒子又是什么……无数个问题堵在胸口,却不知从何问起。奶奶缓缓抬起眼,
目光落在我狼狈不堪的脸上,特别是眼皮上那已经花掉的锅底灰上。
锅底灰……是『他』教你的吧?她喃喃道,语气不是疑问,而是陈述。他?谁?
我猛地想起那些救命的短信,发送人显示是奶奶,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奶奶,
显然对此一无所知。短信……奶奶,那些短信不是你发的?我急切地追问,
挣扎着想从地上站起来,双腿却一阵发软。奶奶摇了摇头,眼神飘向村口的方向,
那里依旧被沉沉的黑暗笼罩着。是守村人。她吐出三个字。守村人?我脑子里一片混乱。
我们村还有守村人?我从小到大从来没听说过!守村人……是村口那缺耳石狮子?
一个荒谬的念头冒了出来。奶奶的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近乎嘲讽的苦笑:石狮子?
那只是镇物,是锁……守村人,是守着这锁,也守着这村子最后一口阳气的人。她顿了顿,
拐杖用力顿了顿地,声音带着一种沉痛:也是……十五年前,没能救下你妈的人。
我妈……真的是死在村口那棵槐树下?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头顶。
十五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声音发颤地问,我妈她……怎么会……
奶奶闭上了眼睛,深陷的眼窝在灯光下显得更加幽深。她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才重新睁开,
眼里只剩下一片死水般的平静。你妈……不是跟人跑了。她缓缓说道,
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是被『选中』了。选中?村里的女人,
每隔一些年头,总会有那么一两个,被『它们』看上。奶奶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
像是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古老传说。吃了供桌上的糯米糕,答应了半夜的叫魂,
就会被标记。你妈……她是不小心,也是被人害了……那天晚上,她听到我在门外叫她,
声音很急……她没多想,就应了一声,开了门……奶奶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哽咽,
但很快又压了下去。门外站着的,不是我。我浑身冰凉,仿佛能看到十五年前那个夜晚,
年轻的母亲打开门,看到门外站着某个顶着至亲面容的恐怖之物时的绝望。
它们把她拖到了村口槐树下……等我们发现时,已经……奶奶没有说下去,
但那未尽之语里的惨状,足以让我想象出最恐怖的画面。那……那刚才门外的……
我牙齿都在打颤。是『它们』扮的。奶奶斩钉截铁,用了你妈残留的『气』,
还有……我的声音。它们想骗你开门,骗你应声,把你彻底拉过去。为什么是我?
我几乎要崩溃,为什么现在又是我?奶奶的目光再次落在那片新土上,
眼神复杂:因为时辰到了。锁快失效了。它们需要一个新的『凭依』,一个血脉相连,
又沾染了『标记』的凭依……你回来了,又吃了那糯米糕……所以,从我踏进这个村子,
不,或许从我收到那封奶奶病重的电报开始,我就已经成了一枚被盯上的棋子?
那木盒子……我看向院子中央。那是你妈的一部分。奶奶的声音低沉下去,
也是阵眼。把它埋在这里,能暂时稳住这院子,让『它们』进不来。但……
她的话没说完,但那个但字,像一块巨石,压在了我的心上。暂时的?守村人呢?
他在哪里?他为什么帮我?我追问,那个发送短信的神秘存在,
此刻成了我心中唯一的希望。奶奶摇了摇头,
脸上露出一丝疲惫的茫然: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已经很久很久没真正出现过了。
或许在祠堂,或许在后山,或许……就在我们身边,用他的方式,守着这最后一点安宁。
她抬起枯瘦的手,指了指堂屋:先进来吧,外面……还不干净。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向堂屋,那昏黄的灯光此刻却显得无比温暖,像一个安全的港湾。
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就在这时——沙沙……沙沙……
一阵极其细微的、像是有人用指甲轻轻刮擦木板的声音,从院门的方向传了过来。很轻,
很慢。一下,又一下。我和奶奶的身体同时僵住。那声音,不是敲门,不是呼喊,
就是这样持续的、充满耐心的……刮擦。仿佛门外的东西知道强攻无效,改变了策略,
用这种缓慢而折磨人的方式,宣告着它的存在,以及……它的不甘离去。
奶奶猛地握紧了拐杖,脸色在灯光下变得极其难看。它们……还没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