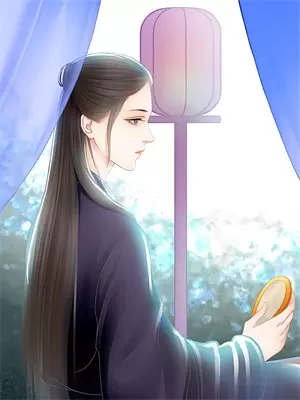我爹是个渔夫,他用一副巨大的鱼骨,拼成了一个女人,还给她穿上了我妈的嫁衣。
雷雨夜后,鱼骨上长出了肉,变成一个不会说话的绝美女人。爹欣喜若狂。
但那女人只吃活鱼,把附近的河都吃空了。后来,村里的猫狗开始失踪。一天早上,
我被隔壁的咀嚼声惊醒。我从门缝看见那个女人,正在啃我爹的胳膊。她发现了我,
对我笑了笑,用我爹的手,朝我招了招。1我爹疯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村里人说的。
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我爹自从我娘走后,就变得不正常。我爹是个渔夫,
一辈子都在跟河打交道。娘走后的第三年,他从下游拖回来一副巨大的鱼骨。
那鱼骨比三四个我还高,惨白惨白的,散发着一股河底淤泥的腥味。“阿水,来看,
”他朝我招手,眼睛里闪着一种我不懂的光,“爹给你再造个娘。
”他把那副鱼骨架在院子里,像搭房子一样,一根一根地拼接起来。他不再打鱼了,
每天就对着那堆骨头敲敲打打。村里的小孩朝我们院子丢石子,喊:“疯子!小疯子!
”我把头埋得很低。我觉得丢人。我爹浑然不觉。他花了半个月,
真的把那副鱼骨拼成了一个女人的形状。骨架很高,比例很怪,但能看出是个人形。
他端详了很久,然后走进里屋,打开了那口尘封多年的樟木箱。箱子里是我娘的嫁衣。
鲜红色的,上面绣着鸳鸯。“爹,你干啥?那是我娘的!”我冲过去想拦住他。“滚开!
”他一把推开我,力气大得吓人。他宝贝一样捧出那件嫁衣,
小心翼翼地给那副白森森的骨架穿上。鲜红的嫁衣套在惨白的骨头上,在风里空荡荡地飘着。
我看着那场景,心里一阵阵发毛。爹却很满意,他绕着鱼骨新娘走了一圈又一圈,
嘴里哼着我娘生前最爱的小调。从那天起,我爹就不怎么跟我说话了。
他每天对着那副鱼骨说话,给它梳不存在的头发,描不存在的眉毛。我觉得我爹不是疯了,
是傻了。心里空了一块,就想找个东西填上。邻居张婶偷偷跟我说:“阿水啊,
你爹这样下去不行,你得劝劝他。”我能怎么劝?我说那是个死物,他抄起扁担就要打我。
他说:“你娘没死,她就是换了个样子陪我们。”我憋着一肚子气,不知道该跟谁说。
我恨那副鱼骨,也开始有点恨我爹。我觉得这个家已经容不下我了。直到那个雷雨夜。
2那天夜里的雷,一个比一个响,好像要把天给劈开。我缩在被子里,吓得不敢出声。
风把窗户吹得哐哐响,雨水斜着打进来。我爹却很兴奋。他没点灯,就坐在院子里,
守着那副鱼骨新娘。闪电亮起的时候,我能看见他仰着头,张着双臂,像在迎接什么。
“阿水!快出来看!你娘要活了!”他冲我屋里喊。我把头蒙得更紧了。
我宁愿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愿相信一副鱼骨会活过来。那一夜,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梦里全是惨白的骨头和鲜红的嫁衣。第二天早上,
我是被我爹的笑声吵醒的。那是一种狂喜的,近乎癫狂的笑声。我心里一咯噔,
爬起来往外跑。院子里,雨停了。空气里都是泥土和水的味道。我爹站在院子中央,
抱着……抱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穿着我娘的嫁衣,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
皮肤白得像水里的浮萍。她很高,比我爹还高一些,眼睛紧紧闭着。是那个鱼骨新娘。
但她身上长出了肉。那肉不是人的皮肤,是一种半透明的,胶质感的东西,
覆盖在每一根骨头上,细腻光滑,甚至能看到下面青色的血管在微微搏动。
“活了……活了……我就知道……”我爹抱着她,又哭又笑。我站在门口,腿肚子发软,
一步也动不了。那女人慢慢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珠是纯黑色的,像两颗光滑的黑曜石,
里面没有一点光。她转动着眼珠,看向我爹,然后又看向我。她不会说话,只是看着。
我爹欣喜若狂,他叫她“阿莲”,我娘的小名。他扶着她走进屋里,
让她坐在我娘生前最常坐的椅子上。他开始叫她“阿娘”,让我跟着叫。我叫不出口。
我看着这个所谓的“娘”,心里只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她不像一个人,
更像一个精美的人偶。她不说话,不笑,不做任何表情。除了饿的时候。3她开始吃东西了。
爹给她做了我娘最爱吃的鸡蛋面。她闻了闻,就把碗推开了。爹又去镇上割了肉,
炖得烂烂的端给她。她还是不吃。家禽,家畜,蔬菜,瓜果,她一样都不碰。
爹急得满头大汗,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有一次,我从河里摸了条小鱼,
放在水桶里忘了拿走。那女人自己走过去,伸手从桶里捞起那条还在活蹦乱跳的鱼,
直接塞进了嘴里。她吃得很快,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吃完,她舔了舔嘴唇,
转头看着我爹。爹先是一愣,然后立刻明白了。“她要吃活鱼!她只吃活鱼!”从那天起,
我爹又开始打鱼了。但他打的鱼不再拿去镇上卖,全都拿回来喂她。她吃得越来越多。
一开始是一天三五条,后来是十条,二十条。她总是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地,
等我爹把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递到她嘴边。她用两根手指捏住鱼头,仰起脖子,
就把整条鱼吞下去,连嚼都不嚼。村子附近的小河很快就被吃空了。鱼越来越难打。
我爹就划着船去更远的下游,有时候天黑了才回来,浑身是泥,
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几条可怜的小鱼。可那根本不够她吃。她饿的时候,
眼睛里的黑色会变得更深。她会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河的方向。
我家的积蓄很快就花光了。有时候,我们一天都吃不上一顿饭,只能喝点米汤。而她,
必须有活鱼吃。我对我爹说:“爹,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会把我们吃垮的!”“闭嘴!
”我爹眼睛通红,一巴掌扇在我脸上,“那是你娘!饿着谁也不能饿着你娘!”我捂着脸,
看着他把最后一条鱼递到那女人嘴边,那女人一口吞下,然后静静地看着他,
眼神里还是那不见底的饥饿。我觉得自己就像那条被吞下去的鱼,无声无息,
连挣扎一下都做不到。憋屈。我恨不得一把火烧了这个家。4河里的鱼彻底没了。
我爹整天整天地坐在门口抽旱烟,唉声叹气。那个女人,那个“娘”,变得很焦躁。
她不再安静地坐着,开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她的眼睛总是盯着门外,喉咙里发出低沉的,类似猫科动物的咕噜声。然后,
村里的猫开始失踪了。先是王大爷家那只养了十多年的老猫,接着是李二婶家刚下崽的母猫。
没过几天,狗也开始不见了。村里人人心惶惶。有人说是黄鼠狼,
有人说是山里的野兽下来了。只有我知道。有天半夜我起夜,看见院子里有个黑影一闪而过。
是她。她嘴里叼着个东西,毛茸茸的,是邻居家的小黑狗。她回到屋里,
角落里传来“咔嚓咔嚓”的骨头碎裂声。我吓得尿都快出来了,连滚带爬地跑回床上,
用被子蒙住头,一夜没敢再睡。我开始害怕她。那种害怕不是以前觉得她怪异,
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一个掠食者的恐惧。我总觉得,她的眼睛在看我的时候,
像是在评估一块肉。我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爹出门的时候,我就跑到村头的老槐树下坐着。
村里的人见我就躲。他们大概觉得我们家不祥。我的世界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我好像被一个透明的罩子扣住了,外面的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我必须做点什么。
这个念头越来越强烈。那天,我爹又划着船去几十里外的野湖捞鱼,说要两天才能回来。
家里只剩下我和她。白天,她还算安静,只是在屋里踱步。到了晚上,她变得异常躁动。
我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用桌子死死抵住门。我听见她在门外走来走去。她的脚步很轻,
像猫一样,但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尖上。然后,我听到了挠门的声音。
“嘶啦……嘶啦……”那声音越来越响,我甚至能听见木屑掉落的声音。她饿了。吃完了鱼,
吃完了猫狗,现在,轮到我了。5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个早上。我爹提前回来了。
他一脸喜色,渔网里装着好几条肥大的活鱼。他进门的时候,那个女人正站在我房间门口。
爹看到她,脸上的笑容更盛了。“阿莲,饿了吧?看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她慢慢转过头,
看着我爹,也看着他手里的鱼。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扑过去吃鱼。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爹,
然后,朝他走过去。她走得很慢,身段摇曳,穿着那身红嫁衣,在清晨的微光里,
有种诡异的美感。我爹被她看得有些不知所措,举着手里的鱼网,憨笑着:“吃啊,
怎么不吃?”她走到我爹面前,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我爹浑身一僵,
整个人都呆住了。这是她第一次主动碰他。他激动得嘴唇都在发抖。然后,她踮起脚尖,
在我爹的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像一个吻。我爹的眼睛瞬间瞪大了,
里面充满了狂喜和不敢置信。就在那一刻。她张开了嘴。一口咬在了我爹伸出来的胳膊上。
没有惨叫。我爹甚至没有挣扎。他就那么站着,脸上还带着那种狂喜的表情,
任由她啃噬着自己的手臂。“咔嚓……咔嚓……”是骨头被咬碎的声音。
血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滴在她鲜红的嫁衣上,颜色融为一体。我躲在门缝后面,浑身冰冷,
牙齿打着颤,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她吃得不快,很有节奏,像是在品尝一道美味。
啃完了一只胳膊,她松开嘴,抬头看向我。隔着那条门缝,我们的视线对上了。她发现了我。
她对我笑了笑,那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笑容,嘴角咧开,露出满是鲜血的牙齿。然后,
她抬起我爹剩下的那只完好的手,朝我,招了招。仿佛在说,下一个,就是你。6那一瞬间,
我脑子里什么都没了,一片空白。身体比脑子反应快。我转身,撞开身后的窗户,
从半人高的窗台上翻了出去,摔在院子里的泥地上。我顾不上疼,手脚并用地爬起来,
疯了一样往外跑。我没敢回头。我甚至不敢去想,我爹是不是还活着。那个招手的动作,
是他自己做的,还是被那个怪物……操控的?我跑出了村子,跑进了山里。
我不知道跑了多久,直到肺里火辣辣地疼,腿像灌了铅一样再也迈不动一步,
才一头栽倒在草丛里。天旋地转。耳边全是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声。那个画面,
那个笑容,那个招手的动作,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地放。她是故意的。她故意当着我的面,
吃掉我爹。她在警告我,也是在邀请我。回到我们这个“家”。我吐了。
把胃里仅有的一点酸水全都吐了出来。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跑了。我爹……我不敢想下去。
但是,我也不能回去。回去就是死。我躺在冰冷的地上,看着灰蒙蒙的天。
我想起娘还在的时候,爹带我去河里摸鱼。他把我扛在肩上,阳光很好,水很清。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眼泪流了出来,和脸上的泥混在一起。我不能死。我要活下去。
为了什么?报仇?我拿什么报仇?一把柴刀,还是我这副瘦骨嶙峋的身子?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必须活下去。我在山里躲了两天,饿了就啃树皮,渴了就喝山泉水。
到了第三天,我实在撑不住了。我知道我必须找人求助。我想到了一个人。村尾的三公。
7三公是我们村里最老的人,老得没人知道他到底多大岁数。他不住在村里,
一个人住在村外河边的一间小木屋里。村里人都说他懂些神神道道的东西,
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或者中了什么邪,都会去找他。但他很少管。我小时候淘气,
去河里游泳差点淹死,是他把我从水里捞上来的。他说我命里带水,让我以后离河远点。